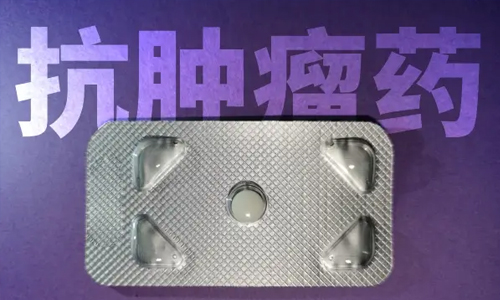孟大庆
在我老家,“桌面”就是上首的主宾方位,自家人一般是不上桌席的,更没有坐“桌面”的道理。
在我儿子周岁生日的宴会上,我让自己的母亲坐了 “桌面”,这成了让街坊四邻津津有味了良久的“新闻”。
村庄里对“桌面”是很考究的,家里有红白喜事,“桌面”一般是给舅舅家的人坐的,或者是让给有必定身份有头有脸的人来坐。关于我母亲这样一辈子在农田里干活,不识几个字的村庄妇女来说,坐“桌面”是一件很不简单的事,只要我姑姑家里有事,我母亲代表姑姑娘家人赴席时才有时机的。因而我母亲对“桌面”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,更对仅有的几回理应坐“桌面”而没有坐成的往事“耿耿于怀”,并视之为对外往来的“羞耻”。
一次是我大姑家的儿子十岁生日,作为我表弟的大舅妈——我的母亲,按老家的风俗理应坐“桌面”,但我城里的两个婶子也去了,大姑很尴尬,以为我母亲好说话就没有组织她坐“桌面”。另一次是我小姑的儿子十岁生日,由于相同的原因,母亲又一次失去了坐“桌面”的时机。
这两件“交际羞耻”让母亲想念了多年,一向想念到我娶妻生子。每逢她想念时,父亲总会不以为然地“哼”一声走开,我忙安慰母亲:“姑姑们就事难呀,更重要的是您通情达理,她们才这样组织的。”我这样安慰时,母亲总说:“你呀,和你老爸一个德性!”长大的我豪情满怀地安慰她:“哪天儿子家有事必定让您坐‘桌面!”这时的母亲笑着说:“面朝黄土背朝天供养你和你妹上了大学,总算听到一句人话。妈不尴尬你,坐不坐‘桌面无所谓了。”
逢年过节,姑姑们齐聚我家时,母亲总是忙里忙外,一大家子人坐在桌上觥筹交错,唯一她没有上桌,他人硬拖也不成。我恶作剧让她坐“桌面”,她更是呵责我“捣乱”,让我招待姑父们上首坐,她则是等他人吃完才胡乱地吃几口完事,忙不迭地拾掇满桌的残羹剩饭,为打牌的众亲朋拾掇“战场”,在麻将的稀里哗啦声里,母亲洗刷一大堆碗筷的声响是那样的冷清孤单。让我铭肌镂骨的是,这样的场景历经多年母亲愣是没有诉苦想念过一句。
我有妻子了,母亲也老了,也不想念坐“桌面”的事了。我成婚那一天,请了全村的人吃喜酒,母亲忙里忙外,顷刻消停的时间都没有。宴席摆了几十桌,竟没有一个座位归于母亲,家里有事,母亲同老家的很多妇女相同,只要料理繁忙的命,甭说“桌面”了,连 叨陪末座的时机都是奢求呀!望着母亲日渐低矮、勤勤恳恳、弓背繁忙的背影,那一天我的心里空落落的,像是欠了母亲什么。
我儿子周岁那天,家里请了厨师,母亲闲不住,终年烧饭、喂猪、剥棉花壳和掰老玉米的手抱着孙子站在门外招待客人。当请客人们入座时,我郑重地提出让母亲坐桌面,母亲连连撤退,不停地摆手,连声说“没有这样的理哎,不可,不可!”母亲惊慌的神态让我心痛:咱们终究对母亲这样的村庄妇女忽视了多久,才会让她对儿子家的“桌面”如此的害怕?
母亲被我请到“桌面”的每一步都是那样的困难,在她儿子忠诚执着的恳求下,一寸寸困难地向“桌面”移动,似乎就是正在走着自己辛苦劳动的终身。当母亲抱着孙子欠了半个身子坐下时,四下里突然响起一片掌声。霎时间,我遽然理解,多年来母亲想念的“桌面”其实就是对她的尊重和注重,可咱们却疏忽了好久。妻子接过母亲怀里的孩子,我扶正母亲,附在她的耳畔说: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比您更有资历坐在这个方位上了!”
一辈子要强的母亲就这样忐忑不安地坐着“朝思暮想”的“桌面”,不时腾出一只手用袖子擦去眼角的泪花。那天母亲不停地承受他人的敬酒,滴酒不沾的她醉了……
zhaozhen1996@sina.com
(修改:赵真)